刚毕业时,曾经蜗居于一座偏远的乡村中学近十年。回想那时的岁月,生活虽然是清苦了些,但其间更不乏兴奋、喜悦、愉快、轻松的记载。
曾经很是孩子气地去追逐密如飞蝗的蜻蜓,也曾经很是忘我地蹲在一棵大树下,低头关注蚂蚁的车轮大战,抬头聆听浓密的枝叶间呢喃的莺歌燕舞。课余饭后,尽情逍遥地享受乡间的那份儿宁静与安适。也许那时正驻足于青春的门槛上,才能够如此这般地感悟到雨的情趣,晴的玄妙。
直到天擦黑依然热闹的像沸水样的大街小巷,是大大小小的男孩、女孩疯玩的景象,有鸡、鸭、鹅、狗的叫声作着伴奏,乡趣与童趣同演。也许他们地处天高荒地远,尚没意识到在“重点”与“非重点”的门槛上,已经四起的狼烟,也许他们一心侍弄庄稼的父母,无暇专注于孩子的记分册,他们才能够如此这般地体验自由的绿洲与纵情的欢歌。
而今自己已年近不惑,在三尺讲台上徘徊久了,也看惯了课桌上堆成的一座座的书山,及从“山峰”空隙间探出的一颗颗挂着高度镜片的脑袋,用“以勤为径,以苦作舟”的古训,谱写着满脸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,力求令所有人都满意地跨过一道道人生的门槛。
此情此景,自己也会默默地叹息,今日考,明日评,循环不断。对这份传道授业的工作,惟独缺少了年轻时候那种音乐般的抒情节奏和诗一样空灵的感觉。
有时候,我会想:矗立在歌吟里,掩映在诗词中,取消以分数为唯一准绳的排队现象,是否也会成功地跨过“素质”与“应试”的门槛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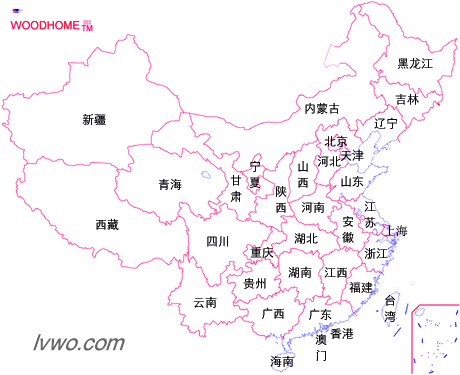


 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...
十大顶级高端户外品牌... 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...
全球户外品牌体系大起... 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...
全球顶级户外人体摄影... 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...
女子裸体户外攀岩性感...